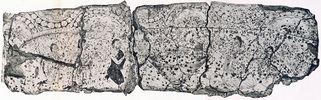本网页由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老师为中心的专家们,结合本网站贵重的文档资料,提供有关丝绸之路的丰富多采的话题。
丝绸之路上的粟特织锦林梅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丝绸的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中国丝绸经中亚大夏(今阿富汗),向南输入印度;向西经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波斯(今伊朗)、大秦(罗马帝国)东境帕尔米拉(Palmyra,今叙利亚),最后抵达罗马城(今意大利罗马城)。 由于丝绸不易保存,前人只能从零星文献记载来了解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和日本考古队在新疆、甘肃等地的探险活动取得一系列重要发现。对于丝绸之路考古来说,这些发现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那些色彩缤纷的中外古丝绸。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 Stein)在楼兰LC墓地发现大批东汉丝绸(插图 1),揭开了丝绸之路出土纺织品研究之序幕。
20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队在罗马帝国东境——叙利亚的帕尔米拉遗址,也发现了东汉丝绸残片[1]。而意大利那不勒斯国立考古博物馆(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 Naples)藏有一幅罗马时期壁画残片,内容表现一个身穿薄纱透体外衣的罗马女祭祀(Menade)。研究者一致认为,这件透明外衣无疑是中国丝绸制作的[2]。这些中国古代丝绸实例,生动反映了汉代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的盛况。 随着丝绸之路的蓬勃发展,公元3世纪起,拜占庭、波斯相继建立了自己的丝绸纺织业,与中国丝绸争夺国际市场。据史书记载:大秦国“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海中[3]。”罗马商人从丝绸之路上安息(帕提亚)商人手中购得中国素丝后,运到地中海东岸近东纺织业中心,按照罗马人喜爱的图案重新织造和染色,然后行销罗马帝国各地。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时,在阿斯塔纳唐墓发现一件拜占庭风格的织锦残片(插图 2)。这件织锦的图案为菱格纹,菱格线上装饰连心纹,菱格内为八角星图案,中心则为十字花。
这块丝绸残片的菱格纹设计,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克赛勒考古博物馆(Kesel Musuem of Archaeology)藏埃及安提诺遗址出土公元3世纪毛织物图案非常相似[4]。梁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记载:“龟兹王为造金师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令什(鸠摩罗什)升而说法”。大秦,是中国史书对罗马帝国或东罗马(拜占庭)的称谓,可知公元4世纪大秦锦就传入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龟兹王国。 罗马和波斯工匠生产的丝绸,采用西方纺织羊毛或亚麻等短纤维的工艺,在丝绸纬线上织花纹;不同于中国织造丝绸的长纤维工艺,在丝绸经线上织花纹,所以西方丝绸称“纬锦”,而中国丝绸则称“经锦”。粟特人不甘心仅仅充当丝绸贸易的中间商,公元5-6世纪开始建立自己的丝绸纺织业。粟特工匠广泛采纳中国、萨珊波斯和拜占庭丝绸图案和西方纬锦纺织技术,后来居上,创造了名闻中外的撒答剌欺织锦(Zandaniji Silk)。 粟特地处中西交通孔道——中亚泽拉夫善河流域。在汉代文献中,粟特称作“康居”,魏晋文献始见“粟特”之名(起初写作“粟弋”)。粟特是个城邦国家,以康国撒马儿干城(飒秣建,今乌兹别克斯坦Afrasiap)为首都;唐代文献统称“昭武九姓”,粟特人则称“九姓胡”。粟特大多数城邦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国,例如:安国(捕喝,今布哈拉)、石国(赭时,今塔什干)、史国(佉沙,今撒马儿干之南)、何国(屈霜你迦,今撒马儿干西北)、竺(呾密,今铁尔梅茨)等;个别城邦则在中亚其他共和国,如米国(弭秣贺,今天塔吉克斯坦国的片治肯特)、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国Ak-Beshim古城)等。 粟特许多城邦都生产丝绸,尤以安国(布哈拉)附近一个小村落——撒答剌欺(Zandaniji)出产的丝绸最为著名。波斯史家拉施德(Rashid al-Din al-Hamdani)《史集》提到1218年蒙古入侵中亚前夕,布哈拉商人与织造撒答剌欺之事。阿拉伯作家纳尔沙希(Naršakhī)在10世纪成书的《布哈拉史》提到这种衣料。他在书中写道:“和撒马儿干人一样,布哈拉人起初是商人以及著名的能工巧匠和织工,尤以从事撒答剌欺布料贸易而闻名于世。这种布料得名于布哈拉城撒答剌欺村,因为它首先在此地织造成功。……这种布料被出口到伊拉克、印度等地[5]。”中山大学教授姜伯勤引用这段史料时,把这个村落译作“赞丹尼奇”。后经清华大学尚刚教授指出,其名当即《元史・百官志》所谓“撒答剌欺” [6]。
13世纪蒙古西征时,野蛮屠杀任何抵抗者,但是有手艺的工匠不杀,蒙古骑兵把一批织造撒答剌欺的能工巧匠驱赶到中国北方的弘州(今河北阳原县)。这些粟特织工归撒答剌欺提举司管辖,为蒙元帝国统治者织造名贵的粟特布料——撒答剌欺[7]。 纳尔沙希的《布哈拉史》只是简单地提到,撒答剌欺是一种布料(cloth),但它没有明说这种布料是什么材料织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人们才终于知道所谓“撒答剌欺”,实际上是一种粟特丝绸。1959年,德国学者舍菲尔德和英国伊朗学家亨宁合撰《撒答剌欺考》,介绍了比利时于伊(Huy)圣母教堂收藏的一件联珠纹对羊纹织锦,长约1.915米,宽约1.22米(比利时于伊教堂藏粟特撒答剌欺织锦(插图 3))。早在1913年,德国古纺织学家冯・发克(O. von Falke)就撰文发表了这件古丝绸,可惜他不认识上面的文字。据亨宁解读,这件织锦上的文字实乃粟特文,年代在公元7世纪,读作:“长61拃,撒答剌欺[8]。”
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吐鲁番绿洲阿斯塔纳古墓发现过一件风格类似的 联珠立鸟纹织锦(插图 4)(Ast.i.6.01),可惜他在报告中误以为是中国工匠织造的“平纹经锦”。瑞典古纺织学家西尔凡后来发现,这件织锦实乃用西方技法织造的“平纹纬锦”。美国古纺织学阿克曼则进一步提出,这件织锦可能是萨珊波斯东部即中亚地方(即粟特)所织造的[9]。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7世纪中叶,吐蕃帝国上层社会流行联珠立鸟纹丝绸外衣。公元634年,吐蕃权臣禄东赞到长安,为吐蕃赞普(国王)松赞干布请婚,迎娶文成公主。唐代宫廷画师阎立本所绘《步辇图》,就表现这个盛大请婚场面。画上禄东赞身穿联珠立鸟和立羊纹织锦长袍(阎立本《步辇图》上身穿粟特丝绸外衣的禄东赞(插图 5))。此画为宋人摹本,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绢本设色,无款,现藏北京国家博物馆[10]。看来,公元7世纪,粟特生产的撒答剌欺锦已行销丝绸之路,并受到吐蕃贵族的追捧。 公元7世纪的粟特织锦,还见于撒马儿干火祆教神殿壁画。画上粟特王拂呼缦手托一匹猪头纹撒答剌欺锦,打算奉献给神庙中粟特火祆教主神。可惜壁画残破过甚,不知庙内主神是何方神圣。关于撒马儿干粟特壁画内容,学界存在很大争议。我们认为,俄罗斯艺术史家马尔沙克(Boris Marshak)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庙内主神是粟特火祆教女神——娜娜(Nania)。因此,这幅壁画上的各国使者不是外交使团,而是前来朝圣的各地火祆教信徒,既包括粟特各城邦的信徒,也有突厥、突骑施、吐蕃等周边国家的信徒。值得注意的是,这幅壁画上还有所谓“中国使团”。确实,这个使团的成员穿汉族服装,但是中国本土无人信仰火祆教。这些汉族打扮的人绝非来自中原地区,而可能是“俗事天神,兼信佛法”的高昌王国派来的使团[11]。高昌王国的统治者麹氏家族是汉族人,所以前往撒马儿干火祆教神庙朝圣的高昌人穿汉服。唐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命侯君集平高昌,那么撒马儿干粟特壁画的年代不晚于公元640年。
20世纪初,俄国奥登堡(S.F. Oldenburg)考察队在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剥走一块联珠含绶鸟纹壁画(克孜尔千佛洞新编第60窟壁画残片,现藏埃米塔什博物馆(插图 6))。这个壁画残片的年代约在公元6-7世纪, 现藏圣彼得堡埃米塔什博物馆。随后,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也来此窟考察,编号为“最大窟” [12], 也即现在编号为第60窟的石窟寺。 近年俄国考古学家马尔沙克根据这个石窟所用颜料和艺术风格指出,这座带联珠含绶鸟纹壁画的佛窟可能是粟特人开凿[13]。他还指出,吐鲁番的吐谷沟千佛洞发现过一幅风格类似的壁画,上面绘有联珠野猪头纹装饰。 这幅壁画是俄国科学院考察队克列门兹(D. Klementz)1898年在吐鲁番考察吐谷沟千佛洞时发现的,出自克列门兹编号的Höle 38窟。德国学者格伦威德尔在中亚考古报告中,为这幅联珠野猪头纹壁画绘制过一幅线图(吐谷沟石窟壁画上的联珠野猪头纹图案(插图 7))。与乌兹别克斯坦国粟特古遗址——公元5-6世纪巴拉雷克・节彼(Balalaik Tepe)壁画上的联珠野猪头纹图案完全相同。这个发现说明,这座带联珠野猪头纹装饰图案佛教石窟,可能也是粟特佛教徒开凿的。
近年吐鲁番博物馆刊布了一件吐鲁番新出土的联珠野猪头纹织锦残片,属于麹氏高昌王国时期(460-640)[14]。由于图案相对完整,可以复原出完整图案(吐鲁番新发现的联珠野猪头纹织锦复原图(插图 8))[15]。这件联珠野猪头纹织锦的图案,与巴拉雷克・节彼壁画和吐谷沟千佛洞联珠猪头纹壁画如出一辙。由此推测,吐谷沟千佛洞联珠猪头纹壁画的年代可能在公元5-6世纪,而非马尔沙克认为的公元7-8世纪。
巴拉雷克・节彼壁画和吐鲁番出土联珠猪头纹织锦的年代在公元5-6世纪,比利时于伊教堂藏粟特联珠对羊纹织锦和吐鲁番出土联珠立鸟纹织锦的年代在公元7世纪,而公元8世纪的粟特织锦,是在塔吉克斯坦国穆格山(Mt. Mugh)古堡遗址发现的。 穆格山粟特古堡位于泽拉夫善河上游,在今撒马尔干城东200公里处,属于粟特城邦米国领地。穆格山城堡出土了许多粟特语文书,有些写在废弃的唐代汉文纸文书上,有些写在木头和皮革上,属于米国统治者的档案,年代在717-719年。我们感兴趣的是,穆格山古堡发现的联珠花卉纹织锦,类似的织锦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亦有发现,为我们研究公元8世纪粟特丝绸纺织工艺提供了重要标本。值得注意的是,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时(1908)在和田南部玉龙喀什河左岸2公里处发现一所粟特艺术风格的佛寺,今称塔里什拉克(Tarishlak)佛寺,平面呈回字形。根据佛寺南壁上的草体婆罗谜文壁画榜题,斯坦因推测它的年代约在公元5世纪。然而,这幅壁画上联珠花卉纹装饰,与穆格山出土粟特织锦图案相同,年代似在公元8世纪初(新疆和田塔里什拉克佛寺联珠花卉纹壁画(插图 9))。
公元10-12世纪的粟特丝织品,大都是在粟特境外发现的。19世纪末以来,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库班河上游古代阿兰人墓地不断发现古代丝绸,先后出土公元6-12世纪丝绸残片200多件,包括唐绢、粟特锦、波斯锦、拜占庭锦和本地产的丝绸。据统计,阿兰墓地所出丝绸60%产于粟特地区;20%产于拜占庭或中国[16]。借助于阿兰古墓的发现,不难发现敦煌藏经洞收藏的古代丝织品中,有许多丝织品属于公元9-10世纪撒答剌欺锦。 斯坦因收集品中有许多包裹佛经的丝绸口袋,时称“经帙”。有些经帙边缘用联珠对狮纹粟特织锦缝制(敦煌藏经洞发现的9-10世纪粟特织锦(插图 10))。由于波斯纳失失(织金锦)名贵,织造不易,既便是元朝皇帝的龙袍,也仅用于领子和袖子边缘,《元史・百官志》谓之“领袖纳失失”。显然,粟特撒答剌欺锦在当时相当名贵,因此,也仅用于经帙边缘。
斯坦因在考古报告中提供了联珠对狮纹粟特织锦图案的复原图(敦煌藏经洞所藏9-10世纪粟特撒答剌欺织锦(插图 11)、其复原图(插图 12)),与欧洲中世纪教堂藏联珠对狮纹锦几乎完全相同。后者原出于法国维尔顿教堂(Cathedral de Verdun),现藏伦敦的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时代约在9-10世纪。
1972年,捷露萨莉姆斯卡亚全面调查了丝绸之路上流行的粟特丝绸。这位俄罗斯女史认为,撒答剌欺锦是一种斜纹纬锦。图案配色与唐锦相仿,但是褪色严重。纹样的组合通常采用“拜占庭式的”严格对称[17]。敦煌藏经洞所藏联珠对狮纹粟特织锦,颇受拜占庭对称艺术影响,堪称公元9-10世纪粟特撒答剌欺锦的典型代表。 (附记:本文插图3、4和8的线图为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研究生陈晓露所绘制,谨致谢忱。)
[1] R. Pfister, Nouveaux textiles de Palmyre découverts par le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u Haut, Commissariat de la République fran aise dans la nécropole de Palmyre, Paris: Editions d'art et d'histoire, 1937;帕尔米拉东汉丝绸与斯坦因楼兰收集品的比较研究,参见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绫、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页1-8;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文集》中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页305-337。
[2] Cf. “Sino-Roman relations”,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
[3] 《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5] Narshakhi, History of Bukhara , trans. by Richard N. Frye, Cambridge, Mass. 1954.
[6] 尚刚:《元代工艺美术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7] 《元史・百官志》卷一记载:“撒答剌欺提举司,秩正五品。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提控案牍一员。至元二十四年(1287),以札马剌丁率人匠成造撒答剌欺,与丝同局造作,遂改组练人匠提举司为撒答剌欺提举司。”另据《元史・百官志》卷三记载,组练人匠提举司设在弘州(今河北阳原县),故知由“组练人匠提举”改建的撒答剌欺提举司设在今天河北阳原县。
[8] D. G. Shepherd, W. B. Henning, “Zandaniji Identified? Aus der Welt der Islamische Kunst. Festschrift fr E. Knhel, Berlin, 1959, pp. 15-40.
[9] Ph. Ackerman, “Textiles Through the Sāsānian Period,” in U. A. Pope and Ph. Ackerman (ed.),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II (Text), Teheran, London, New York, Tokyo: 1938-1939 (reprint 1967), pp. 681-715.
[10]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页229-232。
[11] 关于高昌人“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参见《北史・西域传》、《旧唐书・西域传》。
[13] Boris Marshak, Murals along the Silk Road, Saint Petersburg, 1999, p.70.
[14] 李肖主编:《吐鲁番文物精萃》,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页119。
[15] 参见夏鼐,前揭文,页335,图4-16。
[16] A. Erusalimskaja, “Alanskij Mira na Selkovom Puti,” Kul'tura Vostoka, Leningrad, 1978, pp.151-154.
[17] A. A. Иерусалимская, “К сложению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шелкоткачества в Согде,”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Иран, Ленинград, 1972, pp. 5-46(捷露萨莉姆斯卡亚:《论粟特艺术丝织风格之形成》,埃米塔什博物馆编:《中亚与伊朗》,圣彼得堡,1972年,页5-46)。尚刚教授对捷露萨莉姆斯卡亚的研究作过详细综述,参见尚刚:《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页46-47。
2007年6月15日发行
编辑: 大西 磨希子
|
目录作者 1956年4月生,祖籍广东,生长于北京。70年代后期,在史学家马雍门下受业三年。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考古学,毕业分配至中国文物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其间,师从梵学家蒋忠新学梵语,开展丝绸之路考古和中亚死语言写卷,尤其是犍陀罗语研究。1993年,应美国梵学家邵瑞琪(Richard Salomon)教授邀请,赴华盛顿大学从事中亚死文字研究。1994年,受聘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现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应日本学术振兴会邀请,赴日进行学术交流,任京都佛教大学客座研究员。2001-2004年,三赴香港讲授中外文化交流考古,任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2004年,应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考古艺术系之邀,赴美作学术演讲。
[
更多...
]
索引数字丝绸之路阅览须知
|
您不可以在没有NII许可的情况下以任何方式使用、 复制、再生产、修改、出版、上载、张贴、传送或分发该网站的数码文化资源。